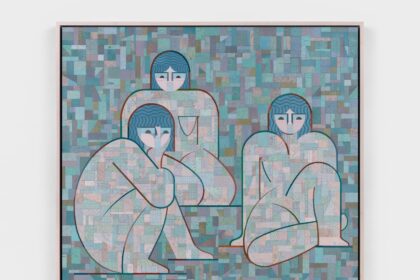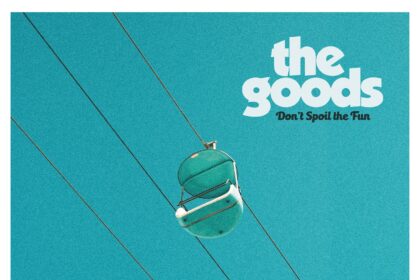对于导演吉勒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而言,《科学怪人》不仅仅是他电影作品中的又一部影片;这是定义了他存在与艺术的旅程的顶点。这是一种他培养了半个多世纪的执念,一个将其线索编织进他以往所有作品DNA的故事。“我为此投入了50多年生命,”这位电影制作人断言,强调他与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的神话之间有着深刻的个人联系。这种执着并非夸张。德尔·托罗坚称,这一基本叙事的元素存在于他所有的13部电影中,并引用他广受好评的《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匹诺曹》,称其为“另一个请求孩子宽恕的浪子父亲”的故事,这正是维克托·弗兰肯斯坦与其创造物之间悲剧性联系的直接回响。
这位导演的痴迷始于童年,七岁时,他观看了由詹姆斯·惠尔(James Whale)执导、波利斯·卡洛夫(Boris Karloff)主演的1931年经典电影《科学怪人》,那是一次启蒙性的相遇。这个最初的视觉冲击在他十一岁阅读1818年的原著小说时,得到了巩固和深化。从那时起,“怪物”(The Creature)已成为他个人神殿中近乎图腾般的存在,一个他近乎视为神祇的形象,一个将其阴影投射到他整个生命与作品上的救世主。艺术与怪物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超越了单纯的电影层面,成为一把解读取他人生的钥匙。德尔·托罗曾谈到他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童年,形容自己是个“喜欢阅读、奇特又苍白的生物”,一个七岁时就研读医学手册、坚信自己身患绝症的疑病症男孩。在卡洛夫扮演的怪物、《哥斯拉》或《黑湖妖潭》等经典怪物身上,他找到了传统世界所否认的认同感。“怪物告诉你,‘看,做自己没关系。不完美也没关系’,”他解释道。他每部充满羊角人、两栖人或木偶的电影,都是对这种“接受不完美”的探索,而《科学怪人》则代表了他一生核心主题的最纯粹、最直接的表达。
这种执念的具象化并未停留在智力或电影层面;它已化为实体。在他著名的“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一个致力于他的艺术和灵感的私人圣殿中,德尔·托罗有一个专门用于《科学怪人》的房间,他称之为“客厅”。在这个被神话人物和相关物品包围的空间里,他写作、研究并进行设计。这种创造者自我封闭,将脑中盘踞数十年的执念赋予物质形态的创作过程,与小说本身的叙事形成了惊人的呼应。因此,这部电影不仅是艺术过程的产物,更是它所讲述故事的主题回响:一个孤独的创造者,为他脑中长久以来的偏执赋予了生命。
哲学愿景:重新诠释“现代普罗米修斯”神话
吉勒莫·德尔·托罗对玛丽·雪莱作品的诠释,刻意偏离了恐怖电影的传统,转而深入存在主义悲剧的领域。对他而言,这部小说具有深刻的哲学复杂性,“与其说是恐怖故事,不如说更接近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他将其描述为“一场对‘何以为人’以及‘存在之痛’的深刻检视”,探索了长久以来困扰人类的根本问题。“在一个非你所愿的世界和存在中诞生”这一核心思想,在他内心产生了深刻的个人共鸣,并与作者本人的精神相连。他形容作者是“一个充满疑问、愤怒和叛逆的少女”,而她的焦虑至今仍是我们的焦虑。
他对这个故事的迷恋植根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他欣赏那个时代“恐怖中蕴含的存在主义美感”。德尔·托罗为这种情感创造了自己的定义,称之为“墓地诗歌”(graveyard poetry),这个词汇精准地概括了阴森与抒情的结合,以及在忧郁与悲剧中可以被发现的美。这种方法颠覆了传统的类型公式。他不是用美来让恐怖变得可以忍受;相反地,他在恐怖之中找到了内在的美。因此,这部电影运用哥特式的框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惊吓,而是为了引发一种“崇高的忧郁”(sublime melancholy),邀请观众在不完美、痛苦和存在的孤独自中沉思美的本质。作曲家亚历山大·德斯普拉(Alexandre Desplat)的配乐也强化了这种情感,他试图清晰地表达“怪物”的“美好情感”,甚至将恐怖的创造场景谱写成一曲“华尔兹”,捕捉了维克托的“创作狂喜”而非行为的恐怖。
这种哲学观也体现在他对文学改编电影的理念上。德尔·托罗寻求的不是字面上的忠实,而是主题上的忠实——将小说的精神转化为电影语言。他用两个强有力的比喻来描述这个过程:改编就像“娶一个寡妇”,也像“一条需要适应陆地的鱼;[…] 必须长出肺”。这两个比喻都表明,原著的精髓必须受到尊重,但它需要根本性的转变,才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媒介中生存和茁壮。这种哲学使他引入的叙事创新(例如扩展创造者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变得合理。这些改变并非对文本的背叛,而是让雪莱的核心主题得以在银幕上“呼吸”所必需的“肺”。因此,这部电影并非书本的誊本,而是通过导演独特感性过滤后,对原著最深层思想的具体体现。
电影的核心:父与子的悲剧
德尔·托罗最重要且最具个人色彩的叙事创新,是将维克托·弗兰肯斯坦与其“造物”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义为冷漠父亲与敏感儿子之间的破碎动态。在玛丽·雪莱的小说中,维克托在“怪物”睁开眼睛后几乎立即惊恐地逃离,但电影引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增加了“一整段童年关系,它开始得相当美好,然后分崩离析”,建立了一种初始的联系,这使得随后的抛弃更具毁灭性。这个决定将冲突的核心从“科学的傲慢”转移到“父爱的失败”,将故事变成了一部具有史诗般哥特式色彩的家庭悲剧。
德尔·托罗强调,这个主题深深植根于他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在拉丁天主教文化中,这是非常沉重的,”他解释道。“对我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父与子的故事。在一个拉丁家庭里,说‘以父之名’就是一切的诞生。”这种观点贯穿了整部电影,探讨了责任、羞耻和对认可的绝望需求等主题。饰演维克托的奥斯卡·伊萨克(Oscar Isaac)回忆说,他曾与导演深入探讨过“那种将孩子视为自身延伸、视为骄傲或耻辱的对待方式”。在这个版本中,维克托的罪过不仅仅仅是扮演上帝,更是作为父亲的根本性失败。他创造生命的动机深深植根于他自己的家庭创伤:对严厉父亲利奥波德(Leopold)(由查尔斯·丹斯(Charles Dance)饰演)的怨恨,因为父亲公然偏爱他的弟弟威廉(William)。维克托创造并非为了科学进步,而是为了验证自己受伤的自尊,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华”。这个“怪物”在他的构想中,是一种自恋的行为,一座旨在证明他价值的奖杯。他随后的排斥不仅仅仅是对怪物的恐惧,更是一个父亲因为“儿子”未能达到他对完美的期望而感到的羞耻。
从“怪物”的角度来看,这段关系就是他存在的全部。饰演“怪物”的雅各布·艾洛蒂(Jacob Elordi)动情地总结道:“对我来说,‘怪物’不可能脱离他的父亲而存在,这就像我和我父亲一样。这是我们所有人与我们父亲的关系。”电影明确地强化了这种联系:“怪物”最初说出的唯一词汇就是“维克托”,这是对他创造者、他的上帝、他的父亲的不断呼唤。在这种诠释下,“怪物性”并非“怪物”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父爱缺失的直接后果”。他生来就带着“一种完全令人卸下心防的纯真、坦诚和纯洁”。塑造他的,是来自世界的拒绝和残酷,而这一切始于他自己的创造者。他的旅程是一场“自我发现”,在此过程中他发展出了良知,并悖论地变得“比维克托本人更具人性”。他最根本的渴望很简单:“爱与被接纳”。他所释放的暴力和复仇,是一个被遗弃的儿子发出的绝望呐喊。通过这种方式,德尔·托罗将怪物性的根源从外表转移到了“抛弃”这一道德行为上——这是一个远远超出恐怖类型界限的普世主题。
主角剖析
在这场情感和哲学的风暴中心,是两位复杂的角色,由导演心目中各自角色的唯一人选饰演。维克托·弗兰肯斯坦和他创造的“怪物”在设计、表演和构思上,揭示了电影愿景的最深层次。
维克托·弗兰肯斯坦(奥斯卡·伊萨克 饰):作为反叛之神的艺术家
作为德尔·托罗扮演主角的“唯一选择”,奥斯卡·伊萨克(Oscar Isaac)赋予了维克托·弗兰肯斯坦一个远超疯狂科学家的形象。他的诠释将其定义为“才华横溢但浮夸自负的科学家”,一个被“战胜死亡、获得永生”的野心所吞噬的“自私”之人。然而,在这种学术傲慢的表象之下,伊萨克和德尔·托罗构建了一个本质上是“被误解的艺术家”的角色。他的实验室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空间,更是一个他可以展演自己才华的“舞台”。他被一种“朋克摇滚的能量”所驱动,渴望“挑衅”那些排斥他的权威体制。
这个浪漫且叛逆的艺术家原型,源于深刻的个人创伤。他的母亲克莱尔(Claire)在生下弟弟威廉时去世,这成为他执着于“战胜死亡”的催化剂。他的野心不断被对专制父亲利奥波德的怨恨,以及对总被视为家中“金童”的弟弟的嫉妒所助长。因此,伊萨克所饰演的维克托并非一个冷酷、精于算计的科学家。他是一个充满激情、以自我为中心、被情感驱使的人物,他将自己的创造物不仅视作科学上的突破,更视作一件终极的艺术品,一个对抗那个从未珍视过他的世界的自我存在宣言。在他的反叛中,他与玛丽·雪莱本人的精神不谋而合——那位将自己的“愤怒与叛逆”倾注于创造永恒神话的年轻女性。
“怪物”(雅各布·艾洛蒂 饰):悲剧性的“人子”
为了塑造他的“怪物”,德尔·托罗摒弃了腐烂尸块拼凑的传统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他寻求一种既令人不安又充满美感的造型。其视觉设计直接基于导演的密友、艺术家伯尼·赖特森(Bernie Wrightson)在1983年为小说绘制的极具影响力的插图。德尔·托罗希望“怪物”看起来像是“新铸造出来的东西”,一种纯粹的新生命形式,“而不是重症监护室里的修补品”。最终的成果被描述为“一个栩栩如生的洁净医学标本,一个拥有轮廓分明肌肉和解剖学上完美的乳白色人体模型”,其人工起源仅由缝合线标示出来。
这个身体成为了一幅深刻神学宣言的画布。“怪物”的形象充满了“天主教意象”,被构想为圣经中“人子”(Hijo del Hombre)的化身。他的诞生是一场“反向的十字架刑罚”,他的身体带着殉道者的圣痕:“象征性的荆棘冠冕”和“如耶稣长矛伤口般在肋侧流泪的伤口”。通过将他呈现为一个并非自然界的错误、而是被世界所腐化的解剖学上完美且纯洁的存在,德尔·托罗将他从怪物提升为一个世俗的基督形象。他是一个被“父亲”(维克托)送到这个世界上的“儿子”,但这个世界不理解他,并因他的“他者性”而将他钉上十字架。他的悲剧不在于他所谓的丑陋,而在于他在堕落世界中的纯真。
雅各布·艾洛蒂(Jacob Elordi)为了这个转变,每天要忍受长达10小时的特殊化妆。他之所以被选中,正是因为他眼中传达出的“纯真与坦诚”。德尔·托罗明确希望这个怪物是“美丽的”,并且具有“吸引力”和“性感特质”。这个决定颠覆了怪物本质上是令人厌恶的前提。通过让他在缝线存在的情况下仍具有身体上的吸引力,这部电影迫使观众去面对偏见的根源。如果“怪物”在客观上并不丑陋,那么他所激起的恐惧必定来自更深层的地方:对非自然、对异类的恐惧。“怪物性”不再是一个美学概念,而转变为纯粹的“社会与心理建构”。
《科学怪人》的世界:角色的生态系统
为了放大关于野心、创造与责任的核心主题,电影在维克托和他的“怪物”周围配置了丰富的配角生态系统。他们每个人都像一面镜子或催化剂,映照并推动着主角的冲突,编织出一幅致密而复杂的叙事图景。
由米娅·高斯(Mia Goth)饰演的伊丽莎白(Elizabeth)尤其关键且多面。高斯承担了双重角色:她不仅是维克托弟弟威廉的未婚妻伊丽莎白,也是维克托那位在分娩时去世的母亲克莱尔·弗兰肯斯坦(Claire Frankenstein)。作为伊丽莎白,她陷入了一场“复杂的三角恋”,对“怪物”展现出同情心,这与他人的恐惧形成鲜明对比,也使她置身于创造者与被造物之间残酷斗争的中心。让同一位女演员来扮演逝去的母亲与爱慕的对象,为叙事建立起强大的心理潜台词。维克托对“战胜死亡”的执念,与一种近乎俄狄浦斯情结的、对母亲形象的渴求交织在一起,并将这份渴望投射到了弟弟的未婚妻身上。
配角阵容众星云集,为维克托的世界赋予了重量与质感。克里斯托弗·瓦尔兹(Christoph Waltz)饰演一个神秘人物,在一些资料中被称为普雷托留斯博士(Dr. Pretorius),另一些则称其为哈兰德(Harlander),他是一位资助维克托实验的“军火商”,为这“苦乐参半的过程增添了一丝轻快”。查尔斯·丹斯(Charles Dance)饰演利奥波德·弗兰肯斯坦(Leopold Frankenstein),维克托那位“威严而专横”的父亲,他严厉且不赞同的形象是驱动儿子野心的动力之一。以《西线无战事》而闻名的费利克斯·卡默雷尔(Felix Kammerer)饰演威廉·弗兰肯斯坦(William Frankenstein),他是家中备受宠爱的“金童”,其存在助长了维克托的自卑情结。演员阵容还包括了小说中的关键人物,例如由拉斯·米科尔森(Lars Mikkelsen)饰演的安德森船长(Captain Anderson)(对罗伯特·沃尔顿船长的重新构想),以及由大卫·布拉德利(David Bradley)饰演的盲人,他为“怪物”提供了短暂的接纳与善意。
创造的艺术:哥特式世界的工艺
吉勒莫·德尔·托罗的电影哲学基于对“工艺”和“实物特效”的深刻崇敬——一种对他在银幕上所创造世界的“可触感”的信念。对于《科学怪人》,这种哲学被发挥到了极致。“我不要数字特效,我不要人工智能,我不要模拟,”导演坚定地宣称,明确表示物质的真实性至关重要。电影的大部分预算都投入到建造大型实景中,包括一个完整的实验室和一艘真实尺寸的船,为每个场景带来了可感知的、仿佛真实存在过的质感。
这种对工艺的执着在他固定的合作团队的作品中显而易见,这群艺术家以卓越的协同效应理解并执行着他的愿景。艺术指导塔玛拉·德维雷尔(Tamara Deverell)曾与德尔·托罗一同前往苏格兰进行实地考察,她是这个哥特式世界的总设计师。她的杰作是维克托的实验室——一个在多伦多搭建的巨型布景,坐落于一座古老的苏格兰石塔顶端,内部充满了华丽的仪器,并由一扇巨大的圆窗主宰。摄影指导丹·劳斯特森(Dan Laustsen)——另一位关键合作者——用光影雕塑了这个世界。他忠于自己的风格,采用了通常来自窗户的单一光源照明、流畅的吊臂摄像机运动,并偏好具有深沉阴影的广角镜头。“我们不畏惧黑暗,”劳斯特森断言。他将这一准则推向极致,在众多场景中仅使用摇曳的烛光作为照明,创造出一种如画般美丽而又压抑的氛围。
艺术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是实现统一愿景的基础。例如,服装设计师凯特·霍利(Kate Hawley)不仅通过强烈的红色和绿色等象征性色彩来设计反映角色心理的服装,还必须与劳斯特森密切配合。一套为米娅·高斯设计的华丽蓝色礼服耗时四个月才臻于完美,这并非因为其复杂性,而是因为需要大量的实验,以确保在摄影机的特定光线下,这种颜色能被正确地捕捉。同样地,亚历山大·德斯普拉(Alexandre Desplat)的配乐也不仅是伴奏,而是叙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将这部电影视作继《水形物语》和《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匹诺曹》之后的主题三部曲的终章,他谱写了抒情且富含情感的配乐,为角色们“未言明的渴望”发声,并使用大型管弦乐团和纯净的小提琴独奏线条,来表达“怪物”最深层的情感。这个团队还包括了剪辑师埃文·希夫(Evan Schiff),他负责掌控视觉叙事的节奏和结构。
这种制作方法,每一个手工打造的元素都依赖于其他元素才能共同赋予整体生命,这本身就是对电影核心主题的强大“元叙事”宣言。电影制作本身变成了一门“弗兰肯斯坦式”的艺术:每个部门都是一个“零件”,必须精确地与其他零件缝合,电影这个“身体”才能作为一个有机且功能齐全的整体,从手术台上站起。形式与内容变得密不可分。
创造与毁灭的永恒回响
吉勒莫·德尔·托罗的《科学怪人》不仅是对经典文本的又一次简单改编,更是一部极其个人化的作品,提炼了他整个职业生涯中始终着迷的主题。通过将玛丽·雪莱的哥特式叙事置于普世家庭悲剧的镜头下,这部电影探索了关于人性、造物主责任,以及在一个排斥我们的世界中寻找身份认同的永恒命题。官方剧情简介将这个故事描述为:“一场骇人的实验,最终导致创造者与他悲剧性的创造物共同毁灭”,这是一条由野心和后果构成的必然轨迹。
通过一丝不苟的视觉工艺、层次丰富的表演以及对核心角色的大胆重新诠释,这部电影有望成为一场对孤独与联结的史诗般忧郁探索。这是一个关于自私科学家的故事,他学到了一个可怕的教训:只有怪物才能扮演上帝;这同时也是一个关于悲剧性创造物的故事,他在自我发现的旅程中,可能变得比赋予他生命的人类更加人性。
这部对野心、孤独以及父子间复杂舞蹈的宏大探索,一个萦绕其导演半个世纪的故事,将于11月7日在Netflix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