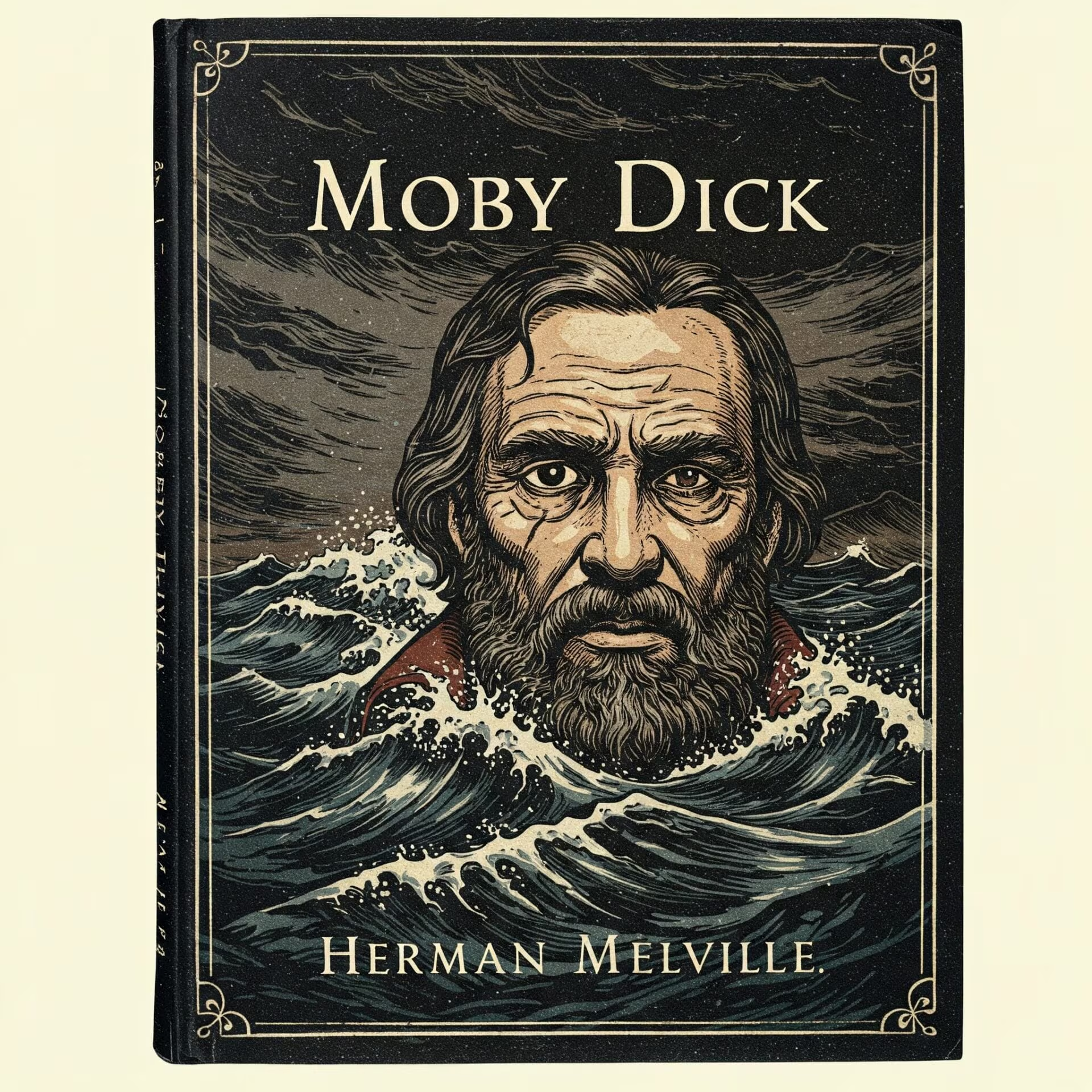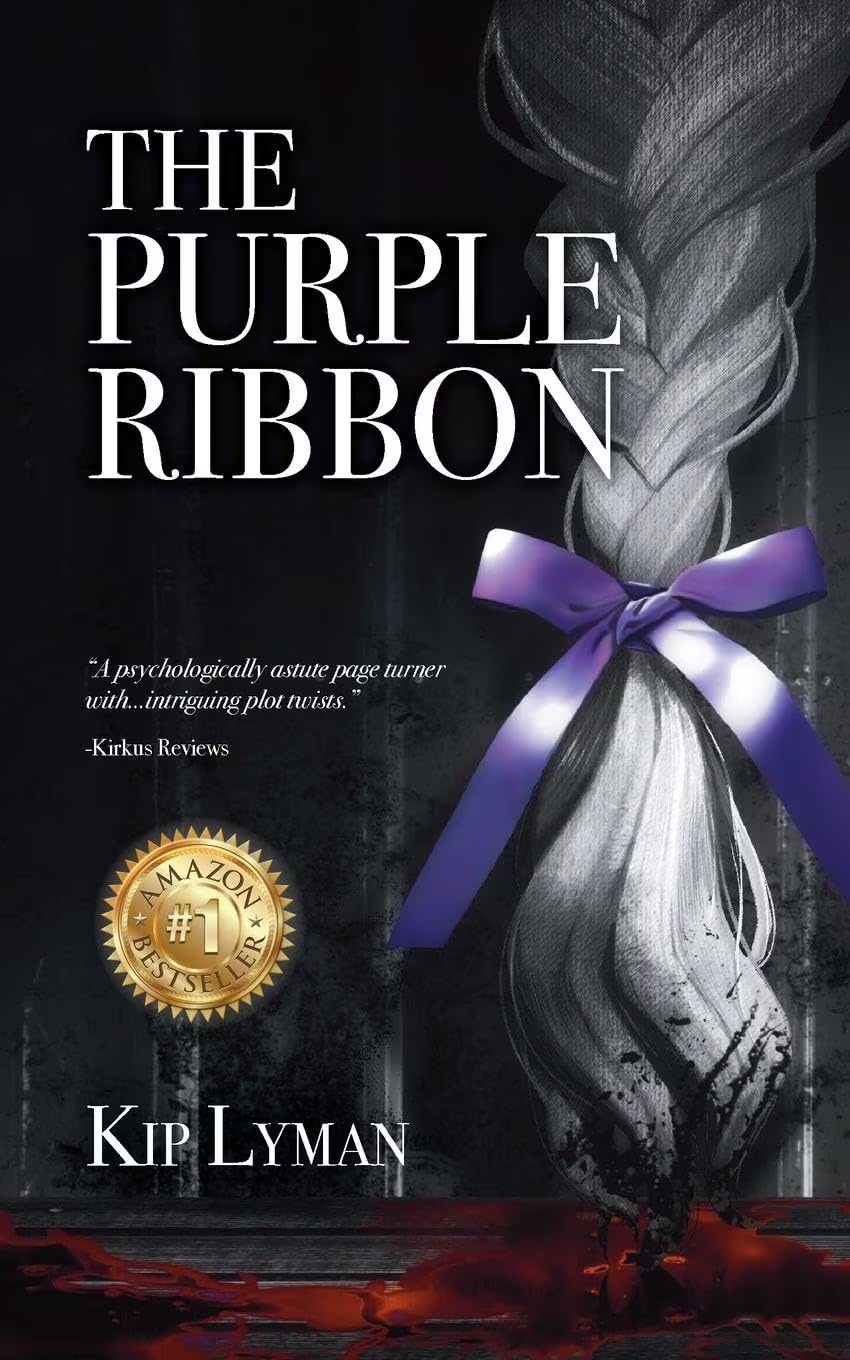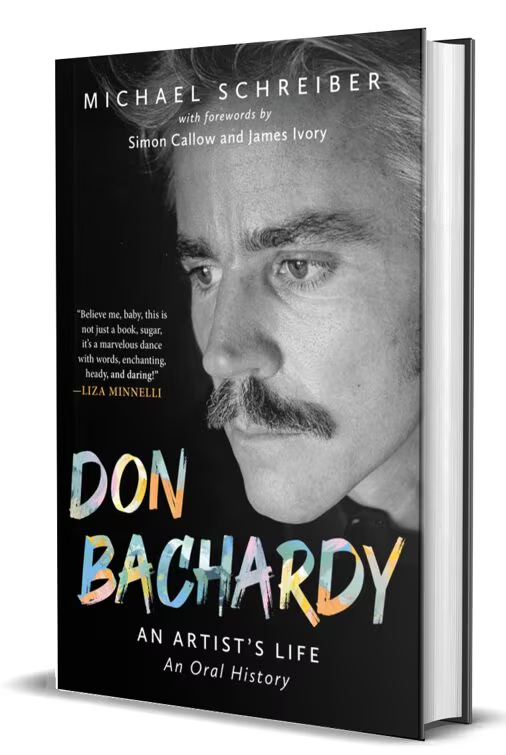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或,鲸鱼》(Moby Dick; or, The Whale)如同一头巨兽,横亘在美国文学的汪洋之中。这部作品深邃莫测,错综复杂,在其问世一个半世纪后,虽最初几乎无人喝彩,如今却依然吸引着我们的目光。它从麦尔维尔在世时商业和评论上的双重失意,转变为如今被尊为世界文学的基石,其历程本身就像“裴廓德号”那命中注定的航行一般引人入胜。这一转变充分说明了小说的持久力量,它跨越代际产生共鸣的能力,以及它几乎如预言般洞察了在其出版数十年后才完全显现的文学与哲学思潮。
白鲸之谜:痴迷的序曲
《白鲸》的悖论:从默默无闻到文学殿堂
当《白鲸》于1851年首次面世时,许多评论家和读者报以困惑、不屑甚至公然的敌意。在麦尔维尔有生之年,它仅售出区区3000册,商业上的失败使其文学声誉日渐衰落。评论家认为其非传统的结构、晦涩的哲学题外话以及黑暗、富有挑战性的主题“荒谬”、“缺乏艺术性”且“古怪”。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这部小说无疑是“一败涂地”。然而,如今,它被誉为对人类境况的宏伟探索,一部集悲剧、哲学探究与深刻寓言于一身的杰作。其开篇句“叫我以实玛利”已成为文学史上最具标志性的话语之一,而亚哈船长偏执地追捕大白鲸的故事也已渗透到全球文化之中。
小说最初遭拒,不仅因其风格的挑战性或公众对捕鲸业热情的消退。更确切地说,其对命运、疯狂以及个体与冷漠甚至怀有恶意的宇宙相对抗等主题的黑暗、存在主义的探讨,似乎预示了20世纪现代主义思想中将出现的焦虑与幻灭。那些曾令同时代读者困惑的元素——其模糊性、对无意义的探索、复杂的心理刻画,以及将自然描绘成“冷漠……且超越人类”——恰恰与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产生了共鸣。这一代人,在世界冲突和旧有确定性崩塌的塑造下,在麦尔维尔错综复杂且常令人不安的视野中,找到了自身存在关切的映照。《白鲸》在某种意义上,等待着它的历史时刻——一个其对人类境况的深刻探究能找到更易接纳的知识氛围的时代,从而促成了它的“重新发现”并最终被奉为经典。
深渊的诱惑:为何《白鲸》仍萦绕我们心头
《白鲸》持久的魅力源于多种元素的强力结合。它是一部史诗般的探索叙事,描绘了一场横跨世界大洋、追捕一种难以捉摸、近乎神话般生物的危险航行。书中人物形象丰满,从沉思的叙述者以实玛利,到“伟大、亵渎神明、如神一般的”亚哈船长,后者的偏执狂热将叙事推向悲剧性的结局。除了惊心动魄的冒险,小说还深入探讨了“存在的深层问题——知识、目的、死亡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麦尔维尔文学事业的宏大抱负,其试图在捕鲸船的方寸之间包容人类经验的全部,持续令读者惊叹与深思。正如一些人所言,它堪比西方文学的奠基之作,试图通过一个人与一头鲸鱼之间毁灭性的仇怨,来直面存在之谜中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
“叫我以实玛利”:在叙事的海洋中航行
漂泊的叙述者:以实玛利的声音与视角
进入《白鲸》黑暗核心的旅程,始于文学史上最令人难忘的邀请之一:“叫我以实玛利”。这一开篇立即确立了一种独特、略带神秘的叙事声音。以实玛利,一名前教师和偶尔的水手,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因深切的不安与存在主义的倦怠而投向大海的人,这是“手枪与子弹的替代品”。他自认是个被遗弃者,一个在海洋的广漠冷漠中寻求冒险,或许还有某种意义的流浪者。在整部小说中,以实玛利不仅是事件的记录者,更是一位充满哲思、观察敏锐、善于反思的向导。他的角色是复杂的;他既是参与航行的角色,也是塑造读者体验的 overarching 意识。他的求知欲和开放的心态,尤其体现在他与波利尼西亚鱼叉手魁魁格不断发展的关系中,使他得以在“裴廓德号”航行的物质与道德险境中穿行,并最终在船只毁灭时幸存下来,他的哲学和对经验的开放性,与亚哈船长那由死亡驱动的痴迷形成对比,证明是能够维系生命的。
以实玛利的叙述本身就是一幅复杂的织锦,将第一手记述与更广泛的哲学思考以及对捕鲸世界的详细阐述交织在一起。麦尔维尔采用了一种流动的叙事视角,常常从以实玛利直接的第一人称体验,转变为一种更具全知性的第三人称视角,从而得以展现亚哈船长孤独的沉思或以实玛利本人未曾目睹的场景。这种叙事的灵活性使麦尔维尔能够在一个远比严格限定视角所允许的更广阔的画布上进行描绘。然而,这也引入了一层叙事的复杂性,以实玛利有时表现为一个“保持距离”的叙述者,一旦出海,更像是一个见证者而非积极的参与者,他的声音偶尔会带有一种似乎“明显是虚构”的特质。正是这种不可靠性或建构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促使读者积极参与阐释过程,而非被动接受单一、权威的叙述。
“叙事大杂烩”:麦尔维尔跨越文体的技巧
《白鲸》以其非传统的结构而闻名,它是一部庞杂的“形式的百科全书,一锅叙事大杂烩”,大胆地挑战了简单的分类。麦尔维尔巧妙地融合了多种文学体裁:它既是惊险的海洋冒险故事,又是深刻的莎士比亚式悲剧,既是晦涩的哲学论文,又是细致的科学手册(尤其体现在其详尽的鲸类学章节中),既是布道与独白的集合,有时甚至像一部带有舞台说明的戏剧脚本。这部小说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出“伪装成小说的戏剧悲剧”,叙事的幕布似乎时而滑落,露出底下的舞台。这种文体的混合性在其时代是革命性的,并且至今仍是《白鲸》独特文学质感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它使麦尔维尔能够从惊人多样的角度探索其多层面的主题——鲸鱼、捕猎、人类境况——极大地丰富了叙事,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的读者预期。
正是这种非传统性——叙事的庞杂、离题和跨文体特征——并非缺陷或仅仅是作者的怪癖,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艺术选择,它映照了小说核心的主题关切,特别是人类知识的局限以及终极真理那难以捉摸、无法把握的本质。小说的结构似乎演绎了它所探索的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正如大白鲸莫比·迪克最终“必定到最后仍无法描绘”,抗拒任何最终的、明确的阐释一样,小说本身也拒绝被简化为单一文体或线性、直接的解读。例如,那些臭名昭著的鲸类学章节,它们煞费苦心地试图对鲸鱼进行分类和编目,可以被视为一种宏大、近乎绝望的努力,试图理解不可理解之物,试图为自然的混乱广袤强加秩序。读者对这些离题、对信息量的庞大以及对声音和风格的不断转换可能感到的沮丧,正映照了角色们自身理解鲸鱼、海洋乃至宇宙的挣扎。一位读者所描述的“捕鲸的‘乏味’的广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主题手段,强调了对知识和意义的艰辛、往往徒劳的追求。这本书,就像那头鲸鱼一样,“向你挑战”,其结构证明了某些真理可能永远超出我们的掌握。
亚哈“不灭的仇恨”:痴迷的剖析
“一个伟大、亵渎神明、如神一般的男人”:亚哈船长的复杂性
在“裴廓德号”的舵盘后,在《白鲸》黑暗的核心,矗立着亚哈船长——文学史上最令人敬畏、也最引人无休止争论的人物之一。船东之一的佩莱格形容他为“一个伟大、亵渎神明、如神一般的男人”,却也“有人性的一面”。亚哈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的角色。他无疑具有超凡的魅力,对船员拥有近乎催眠的力量,然而他却被一种强烈、偏执且最终自我毁灭的“偏执狂式的追求”所驱动,一心要向那头夺去他一条腿的白鲸复仇。他并非一个简单的恶棍;他的思想深度、他富有诗意且强有力的言辞,以及他苦难的巨大程度,都赋予他一种悲剧性的庄严,即便他的行为导致了广泛的毁灭。
亚哈的动机远不止于对身体伤害的单纯复仇。虽然失去腿是其“不灭仇恨”的催化剂,但他对莫比·迪克的追逐转变成一种形而上的反叛。他开始将白鲸不仅仅视为一个特定的、怀有恶意的生物,而是视为“硬纸板面具”,是他所感知到的宇宙中所有难以理解的恶意与不公的可见化身。他的捕猎变成对这些隐藏力量的公然挑战,试图“刺破,刺穿那面具!”去直面其下的现实,无论那现实多么可怕。他追求的这种哲学维度,使其痴迷超越了个人恩怨,将他描绘成一个与存在最深层问题搏斗的人,尽管其方式是毁灭性的,并最终徒劳无功。
船员成为亚哈意志的延伸:同谋与抵抗
亚哈船长高耸的意志和蛊惑人心的言辞,有效地将“裴廓德号”的商业捕鲸航行转变为他个人复仇的工具。船员们,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群,都陷入了他的痴迷之中,他们各自的目的都被他的意志所吞噬。正如以实玛利观察到的:“亚哈不灭的仇恨似乎也成了我的。”这种戏剧性的掌控突显了领袖魅力、心理操纵以及集体行为中往往令人恐惧的动态。船长的固执己见在船上营造出一种紧张、不祥的氛围,因为对利润的追求让位于对一个幽灵般复仇之梦的追逐。
反对亚哈疯狂追捕的主要声音来自“裴廓德号”的大副斯达巴克。作为一名来自南塔基特的贵格会教徒,斯达巴克被描绘成谨慎、有道德且理性的人,一个脚踏实地、笃信宗教的人。他一再挑战亚哈,认为他们的职责是为获取鲸油而捕鲸,而不是沉溺于船长“亵渎神明”的狂怒。斯达巴克是亚哈的重要陪衬,代表了理性与传统道德对压倒性痴迷潮流的抗争。然而,尽管他有自己的信念和勇敢反抗的时刻,斯达巴克最终还是未能使亚哈偏离其毁灭性的航向。他内心的挣扎——在对船长的职责、对船员安全的担忧以及他自己的道德罗盘之间的撕扯——是小说悲剧性发展的核心。他甚至考虑过杀死亚哈以拯救船只,这个念头揭示了亚哈腐蚀性的影响已经深深渗透到即使是最有原则的人心中。斯达巴克未能阻止亚哈,突显了偏执狂的可怕力量,以及抵抗独裁意志的艰难,尤其是当这种意志被如此强大的领袖魅力和可感知的苦难所助燃时。
预言的阴影:费达拉与“裴廓德号”的厄运
为“裴廓德号”的航行增添了一层宿命论和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是一个神秘人物——费达拉,亚哈的帕西人鱼叉手,也是船长偷偷带上船的一支神秘私人捕鲸小队的头领。费达拉“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蒙着面纱的谜”,一个沉默寡言、近乎幽灵般的存在,他是亚哈坚定的随从,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预言家。他发出了一系列关于亚哈之死的神秘预言,这些预言虽然表面上为亚哈的生还提供了条件,但最终却注定了亚哈和“裴廓德号”的毁灭。这些预言——亚哈死前必见海上有两具灵柩,一具非凡人所造,另一具由美国木材制成,且唯有大麻才能致其死地——都在小说灾难性的高潮中得到了残酷的应验。
费达拉的角色超越了一个单纯的预言家;他被解读为“神秘的异己”、“解经的向导”,甚至是邪恶的化身,一个怂恿亚哈走上黑暗道路的魔鬼般的仆从。他对亚哈的追捕表现出坚定不移、近乎超自然的献身精神,以及他时刻沉默地陪伴在船长身边,这些都暗示了一种更深层、更内在的联系。与其说费达拉仅仅是一个外在的“邪恶影响”,不如说他是亚哈自身心理某个基本层面——或许是深层压抑或扭曲的层面——的外化。如果说亚哈是一个反抗他所感知的宇宙不公的人,一个将自己视为“伟大、亵渎神明、如神一般的人”,踏上了“刺穿”现实“面具”的深层内在哲学探索之旅,那么费达拉可能象征着亚哈内心完全屈服于这种黑暗、宿命论世界观的部分。他可能代表了一种败坏的良知或一种虚无主义的驱动力,一个与斯达巴克截然相反的角色,他非但不劝诫谨慎与道德,反而默默地肯定并助长亚哈最具毁灭性的冲动。费达拉那“蒙着面纱的谜”,实际上可能就是亚哈自身最深刻、最可怕信念之谜,是他不屈意志那沉默、阴暗的引擎。
鲸之白,意之深:《白鲸》中的象征主义
莫比·迪克:宇宙的“硬纸板面具”
白鲸莫比·迪克是小说中高耸的核心象征,其内涵如此广阔和多层面,引来了似乎无穷无尽的解读。它远不止是一种生物;它变成了一个“硬纸板面具”,一个角色们——乃至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们——投射他们最深层恐惧、信仰、欲望和痴迷的屏幕。对亚哈而言,莫比·迪克是所有邪恶的化身,“所有那些某些深沉之人感受到在他们内心啃噬的恶意力量的偏执狂化身”。对其他人而言,鲸鱼可能代表自然不可征服的力量、上帝深不可测的意志、冷漠宇宙的可怕虚空,或真理本身难以捉摸的本质。
鲸鱼最显著的特征——它的白色——对其象征力量至关重要。麦尔维尔用整整一章“鲸之白”来探讨其矛盾的本质。以实玛利细致地罗列了在不同文化和语境中,白色与纯洁、无辜、神圣和威严的传统关联——从“天堂里身着白袍的圣徒”的“仁慈”一面,到暹罗白象或汉诺威王朝旗帜上白马的“皇家”内涵。然而,他认为,这种颜色一旦“脱离了更友善的联想,并与任何本身可怕的事物相结合”,就会变成恐怖的“强化剂”。他指出,北极熊或大白鲨的白色,放大了它们的恐怖。因此,在莫比·迪克身上,白色超越了其传统象征意义,唤起了一种深刻的存在主义恐惧。它可以象征“充满意义的沉默空白”,一种可怕的空虚,“宇宙无情 的空洞与广袤”,剥去了色彩和意义的慰藉性幻象,揭示出一种潜在的、或许是混乱甚至怀有恶意的现实。这种模糊性,这种白色既能体现崇高又能体现恐怖,既能体现神圣又能体现亵渎的能力,使得莫比·迪克成为宇宙终极奥秘取之不尽的象征。
“裴廓德号”:一艘漂流的末日之船
捕鲸船“裴廓德号”,小说大部分情节展开的地方,其本身也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它以一个被欧洲殖民者消灭的美洲原住民部落命名,其名称本身就带有不祥的毁灭预兆。这艘船被描绘成老旧不堪,饰以鲸骨和鲸齿,使其呈现出一种阴沉、近乎葬礼般的气氛——一具“漂浮的残骸”,驶向其末日。船上有着来自世界各地、代表着多种族和信仰的多元化船员,“裴廓德号”因此成为人类社会的缩影。它是一个微型世界,一个上演人类雄心、愚行和友谊的宏大戏剧的舞台。在亚哈的指挥下,这个漂浮的社会偏离了其商业目的,转变为一艘复仇之船,象征着在一种吞噬一切的非理性痴迷驱动下,人类的集体命运。它的航行也可以被视为代表了19世纪工业野心的不懈驱动,特别是捕鲸业本身的剥削性质,不断向未知水域推进以追捕其猎物。最终,“裴廓德号”是一艘末日之船,其命运与船长及其追捕的白鲸密不可分。
海洋:“生命中不可捉摸之幻影的意象”
海洋为“裴廓德号”的悲剧航行提供了广阔而冷漠的背景,它同样也作为一个深刻的象征而存在。以实玛利本人曾著名地反思过水的磁力,他说“沉思与水永远联姻”。《白鲸》中的海洋代表了潜意识,“生命与上帝从中产生的巨大混沌”。它是一个拥有巨大力量、美丽与恐怖的领域,体现了自然对人类努力的崇高冷漠。海洋是一个“两栖”的存在,时而显得宁静诱人,时而揭示其狂野、危险和毁灭性的能力。它隐藏着未知的深度与真理,映照着鲸鱼本身——其巨大的身躯大部分都隐藏在视线之外。对以实玛利而言,海洋是“生命中不可捉摸之幻影的意象”,一个上演着存在最深奥秘的领域,而那些胆敢航行于其广袤之中的人,往往要付出残酷的代价。
达布隆金币:灵魂之镜
一个特别富有象征意义的片段出现在题为“达布隆金币”的一章中,亚哈将一枚厄瓜多尔金币钉在“裴廓德号”的主桅杆上,作为第一个发现莫比·迪克的人的奖赏。当不同的船员走近并仔细观察这枚金币时,他们的解读更多地揭示了他们各自的本性、信仰和关注点,而非金币本身。斯达巴克在其图像中看到了一个阴沉的宗教寓言,反映了他对这次航行亵渎神明性质的焦虑。务实的斯塔布则从中找到了一个愉快而宿命论的信息。唯物主义的弗拉斯克只看到了它的货币价值——十六美元,或“九百六十支”雪茄。亚哈本人,在一个深刻洞察的时刻宣称:“这枚圆形的金币不过是更圆的地球的影像,它就像魔术师的镜子,依次向每一个人映照出他自己神秘的自我。”
这一章巧妙地探讨了主观性及阐释行为本身。《白鲸》中的达布隆金币成了一块空白的画布,其意义是建构而非固有的,完全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这一场景为小说本身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元评论。“裴廓德号”船员对达布隆金币的不同解读,直接预示了几个世纪以来评论界和读者对这部小说产生的多样化阐释。正如每个水手都将自己的世界观投射到金币上一样,文学评论家和读者也将无数的意义投射到麦尔维尔复杂的文本上。斯塔布的评论“现在有了另一种解读,但文本依旧是同一个”明确地强调了船员们的阐释实践与更广泛的阅读行为之间的联系。这部小说作为一部能够产生“无数解读”的“活文本”的持久地位,在“裴廓德号”上这个意义建构的微观世界中得到了预示。因此,麦尔维尔展现了一种成熟的作者自我意识,在他的叙事中嵌入了对文本获取意义的主观且持续过程的反思。
麦尔维尔的熔炉:捕鲸、经验与文学技艺
“一次捕鲸航行是我的耶鲁学院和我的哈佛”:麦尔维尔的航海生涯
赫尔曼·麦尔维尔对海洋和捕鲸生活的深刻理解并非源于学术研究,而是来自直接的、往往是艰苦的个人经历。1841年,他签约登上捕鲸船“阿库什尼特号”开始了一段航行,这段经历为他提供了关于19世纪捕鲸业的实践、危险和人情世故的宝贵教育。这种第一手知识为《白鲸》注入了无与伦比的真实性和丰富的生动细节。他对捕鲸复杂过程、鲸脂剥取和熬油、捕鲸船上错综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船员所面临的纯粹体力劳动和持续危险的描述,“全面而毫不畏缩地准确”。麦尔维尔将他的经历转化为“对捕鲸业的文学致敬”,既捕捉了其残酷的现实,也展现了其奇特而引人入胜的魅力。此外,他还深受“埃塞克斯号”捕鲸船真实故事的影响,该船于1820年遭到一头抹香鲸的袭击并沉没——这一叙述为他小说的核心冲突提供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先例。这种植根于亲身经历和历史记载的基础,即使是故事中最富幻想色彩的元素,也赋予了强大的逼真感。
巨兽的语言:麦尔维尔的独特风格
《白鲸》的文学风格如同它所追逐的生物一样广阔、多样且强大。麦尔维尔创造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散文风格,它是高雅辞藻与粗俗口语的丰富融合,是深奥哲学段落与惊险即时动作场景的结合。他的语言“航海的、圣经的、荷马的、莎士比亚的、弥尔顿的、鲸类学的”,证明了他广泛的阅读和他创作一部真正美国史诗的雄心。他拓展了语法的边界,引用了各种来源,并且当现有的英语词汇不足以表达他希望表达的复杂细微差别时,他毫不畏惧地创造新词和短语。这种语言上的创造力——创造新的动名词如“coincidings”(巧合之事),不熟悉的形容词如“leviathanic”(巨兽般的),甚至从名词创造动词如“to serpentine”(蜿蜒而行)——赋予他的散文一种动态、强劲的特质,完美地契合其宏大的主题。
莎士比亚的影响尤为深远,不仅体现在直接的引经据典上,也体现在某些场景的戏剧结构中,最显著的是在亚哈船长那些常常可以视为无韵诗的独白和演说中,其高亢、富有诗意的语言赋予了角色一种悲剧性的、近乎神话般的地位。圣经的韵律和典故也渗透在文本中,赋予叙事一种道德分量和预言般的紧迫感。
穿插在这丰富文学织锦中的是备受争议的鲸类学章节——关于鲸鱼解剖、行为和历史的详细、往往冗长的论述。虽然一些读者认为这些部分是乏味的离题,阻碍了叙事的流畅性,但它们对于麦尔维尔百科全书式的雄心以及他对人类知识局限的探索是不可或缺的。这些章节代表了通过科学话语来把握、分类和理解鲸鱼的尝试,然而它们最终强调了这种生物的终极神秘性以及人类体系在完全理解自然世界方面的不足。正如以实玛利所进行的分类行为一样,它成为人类即使面对深不可测之物也需要寻找秩序和意义的一种隐喻。
深渊中的回响:《白鲸》的持续航行
从被忽视到“麦尔维尔复兴”:一场文学的复活
《白鲸》的评论接受史本身就是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其特点是最初的被忽视和死后非凡的复活。如前所述,这部小说在麦尔维尔生前基本上被误解,商业上也不成功,导致他逐渐淡出文坛。在他1891年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如果人们还记得麦尔维尔,那也主要是因为他早期更传统的南海冒险故事,如《泰皮》(Typee)和《奥穆》(Omoo)。
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初,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现在所称的“麦尔维尔复兴”。这种兴趣的重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化气候的变化、文学现代主义的兴起(其欣赏复杂性和模糊性),以及新一代学者和评论家的不懈努力。这次复兴中的关键人物包括雷蒙德·韦弗,他1921年的传记《赫尔曼·麦尔维尔:水手与神秘主义者》将这位作家及其富有挑战性的杰作重新带回公众视野;还有像D.H.劳伦斯这样的有影响力的作家,他在其《美国经典文学研究》(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1923)中称赞《白鲸》是“一本无与伦比的美丽的书”。评论家们开始欣赏小说的深刻象征意义、心理深度、创新的叙事技巧以及对存在主义主题的大胆探索——这些特质曾使其最初的读者感到疏远,但却与现代主义情感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刘易斯·芒福德1929年的传记进一步巩固了麦尔维尔日益增长的声誉。这次复兴不仅将《白鲸》从被遗忘的边缘拯救出来,也导致了对麦尔维尔全部作品的更广泛重新评估,并从根本上重塑了美国文学的经典体系,挑战了其先前以新英格兰为中心的焦点。
白鲸的航迹:对文学、艺术和文化的持久影响
自复兴以来,《白鲸》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和流行文化投下了悠长而持久的阴影。其主题、人物和标志性意象启发了不同媒介中无数的艺术家。从诺曼·梅勒(其《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有意识地呼应了麦尔维尔的作品)到科马克·麦卡锡和托妮·莫里森等当代作家,都承认其影响。小说的核心冲突、哲学深度和复杂人物为创造性的再阐释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视觉艺术领域,《白鲸》催生了众多的插图版本,并启发了画家和雕塑家。罗克韦尔·肯特为1930年湖滨出版社版所作的醒目插图成为经典,而像杰克逊·波洛克和弗兰克·斯特拉这样的艺术家也创作了借鉴小说主题和章节标题的重要作品。最近,马特·基什承担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为小说的每一页创作一幅画。
亚哈与白鲸的故事也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从早期的默片如《海兽》(The Sea Beast)(1926年)到约翰·休斯顿执导、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著名1956年改编版。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对《白鲸》的提及,出现在音乐(齐柏林飞艇的器乐曲“Moby Dick”,MC Lars的说唱“Ahab”)、幽默作品(盖瑞·拉森的漫画)甚至像《星际旅行》(Star Trek)这样的电视剧中,其探索主题与麦尔维尔本人的主题产生共鸣。小说的情节和主要人物已深深植根于我们的集体文化想象之中,这证明了其原始的叙事力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
21世纪的《白鲸》:当代的批评视角
对《白鲸》的阐释之旅远未结束。在21世纪,通过当代文学理论的各种视角审视这部小说,持续产生新的见解。精神分析的解读探索了像亚哈这样的角色的深刻心理层面,将其追寻视为根深蒂固的创伤或压抑欲望的表现,并将“裴廓德号”本身视为集体人类心灵的容器,充满了焦虑、恐惧和固着。后结构主义的方法,特别是那些受德里达解构主义影响的方法,关注文本内意义的不稳定性,考察像达布隆金币这样的象征,以说明意指作用是如何在差异的无尽游戏中进行的,没有最终的、固定的中心。
生态批评的阐释在亚哈对鲸鱼的无情追逐中,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隐喻,象征着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往往具有破坏性和剥削性的关系。19世纪的捕鲸业本身被视为现代资源枯竭的先兆,而莫比·迪克可以被解读为自然在人类狂妄自大面前的激烈抵抗或其崇高冷漠的象征,这些主题在气候危机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时代,尤具紧迫的共鸣。
后殖民主义的解读审视了小说对其跨国和多种族船员的描绘,探讨了像魁魁格、塔什特戈和皮普这样的角色是如何通过叙述者往往以欧洲为中心的凝视以及19世纪的社会规范来呈现的。这些分析深入探讨了殖民主义、种族等级制度、对非西方文化的“他者化”以及奴隶制的阴魂不散等主题,在“裴廓德号”这艘船上找到了全球权力动态和文化交锋的浓缩场所。这艘船及其多样化的居民——高级船员通常是新英格兰白人,而前甲板则挤满了各种族和国籍的人——成为审视再现、剥削和身份建构等问题的迷人(尽管不完美)空间,这些问题与当代多元文化和后殖民话语仍然高度相关。麦尔维尔对这些“底层”人物的描绘,虽然经过了他那个时代的滤镜,但为批判捕鲸业在全球范围内所代表的帝国事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与此同时,酷儿理论的阐释则探讨了“裴廓德号”这个全男性社会中强烈的男性情谊,特别是以实玛利和魁魁格之间深刻且往往带有模糊情色意味的关系。这些解读审视了在一个几乎没有女性的世界中,同性社交、同性情欲、对认同的渴望以及男性气概的展现等主题,并常常强调这些关系在19世纪背景下的种族化维度。
《白鲸》能够承受如此广泛的批评性阐释,证明了其非凡的复杂性以及它拒绝提供简单答案的特质。每一种新的理论方法似乎都能揭示出更深层次的意义,确保麦尔维尔的这部杰作仍然是文学探究中一个至关重要且引人入胜的课题。
对意义的无尽探求
《白鲸》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是一种体验,一次挑战、激发并最终改变读者的智力与情感之旅。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它的丰富性“每读一次都会增加”。如同亚哈对白鲸不懈的追逐,读者对《白鲸》明确理解的探求,最终可能也是永无止境的。小说探讨了“存在的最深层问题”,其深刻的模糊性确保了其最终的“意义”如同莫比·迪克本人一样难以捉摸且多层面。然而,恰恰是这种难以捉摸性,其产生似乎无限多样的阐释的能力,才是这部小说持久力量之所在。穿越其晦涩的散文、哲学的深度和萦绕心头的叙事的旅程,本身就是一种回报。《白鲸》依然是一部深刻而不平静的杰作,一头文学巨兽,继续航行在我们想象的海洋中,邀请每一代新人踏上在其书页中探寻意义的无尽征程。